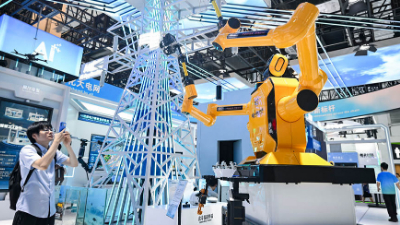清代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分省图。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深褐色樟木柜中,静静躺着数千幅古地图。它们或绘于绢帛,或刻于石碑,或印于纸页,有的残缺斑驳,有的依然色彩鲜艳——这些被岁月封存的“历史切片”,不仅是地理信息的载体,更是中华文明的“立体档案”。
近日,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《天地之间: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》,以这些古地图为“钥匙”,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。从战国铜版到清代绢图,从“计里画方”到经纬度实测,书中50余幅经典古地图的“复活”,不仅让我们看到古人如何认知世界,更解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创新。
古地图:被折叠的历史长卷
地图不是冰冷的工具,而是古人对世界的“回答”。这些看似静态的图形,实则是动态的历史记忆——它们记录了疆域的伸缩、技术的进步、文化的交融,甚至藏着古人的情感与想象。
战国中山国的铜版《兆域图》,是书中开篇的“主角”之一。1974年出土于河北平山的它,长94厘米、宽48厘米,表面因墓葬火烧而凹凸变形,却依然清晰可见用金银丝镶嵌的线条与铭文。“兆”即墓域,这是中山王为自己规划陵园的建筑蓝图。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建筑规划图,更是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。
比《兆域图》晚约400年的西汉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》,则展现了古人对“现实空间”的精确认知。这幅绘于绢帛的地图,长97厘米、宽93厘米,以1∶18万的比例(约合汉代“一寸折十里”)描绘了长沙国南部的山川、城邑与道路。图中30余条河流的走向与现代卫星地图高度吻合,80余个居民点以矩形(县城)和圆形(乡里)符号区分,20余条道路用虚实线标注。根据相关学者考证,图上所绘制的河流骨架、流向及主要的弯曲等,和今日的实际情况大体相似,这也证明《地形图》是一幅经过科学测量的地图。
如果说《兆域图》是“微观空间”的秩序、《马王堆地形图》是“区域空间”的写实,那么宋代《禹跡图》则开启了“宏观空间”的探索。现存于西安碑林的《禹跡图》石碑,刻于南宋绍兴六年(1136),图上以“计里画方”法绘制了255个方格,每格“折地百里”,横70格、纵73格,覆盖了“九州”的核心区域。
“计里画方”相当于古代的“经纬网”,通过网格定位,让地图从“示意图”变为“实用图”。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评价它“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”。它的出现,更推动了后世《广舆图》等大型地图集的诞生。
明代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的出现,是中国古地图史上的一次“裂变”。这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,以椭圆投影法呈现全球,首次将“地圆说”“经纬度”引入中国。但它并非“西方中心”的复制——为了让中国读者接受,利玛窦调整了投影,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;山脉用青绿山水法绘制,河流以双曲线表现,与传统舆图风格一致。利玛窦知道,要让中国士大夫接受新的地理观,必须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与符号。这幅地图的彩绘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,虽仅存一条屏(亚洲部分),但仍可见海洋用浅灰波纹填充,山脉以立体形态勾勒。它既是科学的,也是艺术的,更是跨文化对话的见证。
与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的“开放”不同,清代《福建舆图》则以“宏大”诠释了“疆域主权”。这幅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绢本地图,长7.5米、宽7.5米,四周以黄缎镶边,绣有9条金龙,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单幅绢本地图。图中详细绘制了福建九府一州的疆界、城池、关隘,甚至台湾府的“诸罗县”“凤山县”也被清晰标注——“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台湾正式纳入福建管辖,这幅图正是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时刻而绘制。”图中用红色单线标府界、绿色标县界,道路以黄底红条纹表示,这种标准化的符号体系,说明清代已形成成熟的行政地图绘制规范。
地图里藏着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
古地图的绘制,从来不是单纯的“技术行为”。从符号选择到内容取舍,从命名逻辑到绘图风格,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的价值观与文化基因。
南宋黄裳为嘉王赵扩(后来的宋宁宗)绘制的“天地人三图”——《天文图》《地理图》《帝王绍运图》,是书中诠释“宇宙观”的典型案例。《天文图》刻于石碑,上半部分为星图,标注了1400余颗恒星,涵盖三垣二十八宿;下半部分为图说,系统讲解“天体圆、地体方”“日为德、月为刑”的哲学;《地理图》则绘制了宋代疆域,标注了400余处府州县,图跋中写道“中原土壤,北属幽燕,以长城为境旧矣”,暗含收复失地的期许;《帝王绍运图》以图表形式排列自黄帝起的帝王世系,评说盛衰之理。
三图并列,正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具象化表达:天有星象,地有山河,人有历史,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宇宙秩序。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,更是价值观的灌输——嘉王后来成为宋宁宗,或许正是这些图激发了他“修德行政”的理想。
明代《山西镇总图》《宣府镇总图》等“边镇图”,则是“家国同构”的缩影。这些地图以形象画法绘制了九边重镇的边堡、关隘与山川,山西镇的“宁武关”“雁门关”,宣府镇的“张家口堡”“独石城”等,均用醒目标注,旁注驻军人数、粮秣储备。
边镇图不是普通地图,而是军事防御的“活档案”。《宣府镇总图》中“张家口堡”标注“朝往夕返”“远商辐辏”,既记录了军事功能,又反映了边贸的繁荣;这些地图不仅是防御工具,更强化了“守边即守家”的国家意识。
明代《河防一览图》则以“治河”诠释了家国情怀。这幅由治河专家潘季驯主持绘制的长卷,纵43厘米、横2010厘米,详细标注了黄河从星宿海到入海口的河道、堤坝与水患点,甚至记录了“束水冲沙”的治河策略。潘季驯4次治河,这幅图是他经验的总结。
图中“祖陵图说”“皇陵图说”强调黄河对皇家陵寝的保护,但实际上治河不仅是民生工程,更是“护陵”“护国”的政治任务。图中大量标注的“民埝”“官堤”,则体现了“官民共守”的治理智慧——古人早已知晓,大河安则家国安。
中华文明的延续,还在于对“空间”的认知与守护
书中大量引用国图藏珍稀舆图,如世界最大绢本《福建舆图》、清代《云南全省舆图》(26册,含102幅分图)、明代《全海图注》(记录沿海卫所与倭寇防御)等。这些地图多为首次系统整理,部分甚至从未公开出版。例如,《云南全省舆图》分“全省总图”“府厅州总图”“县分图”三级,比例尺从“百里方”到“十里方”,这是清代官方测绘的典范。每幅分图都附“图说”,记录疆域四至、人口、赋税,堪称“清代云南百科全书”。
书中避免了晦涩的专业术语,转而以“故事化”叙述激活古地图。例如,讲述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时,作者不仅介绍其“首次实测珠穆朗玛峰”“验证地球扁圆说”的科学成就,更还原了测绘背后的细节。
康熙四十年(1701),传教士安多等人先在北京周边试测,康熙帝将结果与旧图对比,发现新图更精确,才敢展开全国测绘;测绘队用“三角测量法”翻山越岭,在西藏最早发现并测绘珠穆朗玛峰,比印度测量局早135年。这些细节让地图不再是“死物”,而是一群人用脚步、仪器与智慧写就的“流动的历史”。
书中特别关注古地图对当代的启示。例如,《郑和航海图》记录了30余国的航线,标注了“满剌加”(马六甲)“古里”(卡利卡特)等地名,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高度重合;《乾隆十三排图》以经纬度网格标注新疆,与今天的“国家版图意识”一脉相承;《五岳真形图》的符号被现代设计师借鉴,成为“中国风”文创的灵感来源。古地图不仅属于过去,更连接着现在与未来。
从战国铜版上的“兆域”到清代绢图中的“天下”,从“计里画方”的传统到经纬度实测的科学,《天地之间:古地图中的中国故事》以舆图为线,串起了一部“看得见的中国史”。这些被岁月磨洗的古地图,不再是“故纸堆”里的旧物,而是会说话的“历史证人”——它们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,也告诉我们:中华文明的延续,不仅在于文字的传承,还在于对“空间”的认知与守护。(白鸿叶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组长,研究馆员)